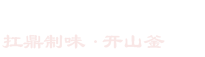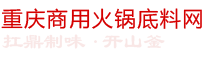大部分人以为拿胃和这座荣膺“海洋美食之都”的山东城市走心的方式,是把劈柴院的美食吃到窜稀,是对青啤一厂口味棒二厂易上头的江湖规矩如数家珍,是每日聚集在王姐烧烤面前等待的那串烤鱿鱼。
殊不知如果没在深夜的马路牙子上嗦上一碗胡椒粉过量的野馄饨,你还是等于没有来过青岛。
即便拉着本地人赞美德国人修建百年下水道留下的油包纸,你也只能从当地人牙缝里勉强挤出的“嗯嗯”回应里感受到一丝“我原谅你”的礼仪。
这种尴尬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人和一个喜欢以“游客方式”提问的无聊朋友。


而属于青岛的尴尬,是在微信上互道晚安,却相遇在野馄饨摊。
作为国民小吃,馄饨太过普适,牢牢占据着北方人民心目中的早餐一席。
但在青岛,它却是夜的代名词。


因为,不在深夜11点后才开始营业的馄饨摊不叫野馄饨。
在这座经济发达的海滨都市,皮包和口红俘获不了青岛小嫚的芳心,只有在野馄饨摊为女孩排过队的男人才有机会。
撩起的那层纸薄的馅皮,是她和这座城市的秘密徐徐向你展开的帷幕。
归乡的游子会在第一时间呼朋引伴,不顾路途疲惫,加入馄饨摊排队的大军之中。直到感受温润的海风拂面,行道树的的落叶被吹进掉落汤头,才算是终结了一路风尘仆仆攒下的乡愁。
每一个被鲁B牌照包围的街头脏摊,都是青岛夜的灯塔。
对青岛人来说,吃野馄饨最难之处不是排队,而是停车。
你不知道,为了这一口馄饨,有多少本地人不惜堵车几个小时,从李沧区赶到市北区,区区半小时的排队对于他们来说,是应该给到野馄饨的尊重。
本地人要解决的乡愁对于外地人来说却是一种距离,野馄饨摊的外地游客比例极低,坐在塑料小马扎上把馄饨吸到滋溜作响的,都是说话习惯倒装的青岛街坊。
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容易淹没在馄饨汤头的蒸汽之中,作为外地人的你若不能有模有样的说几句青岛方言,可能连菜都点不上。
你永远猜不到青岛人有多么需要野馄饨。
对青岛人来说,只有馄饨摊,才是所有夜晚故事的伊始。
作为每到年关,必然隆重登场的最新野馄饨地图,也是本地自媒体争先抢夺的美食领域话语权之争。
这种风味名小吃一直就是“青岛生活”的流量万金油。
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,即便信息的媒介从纸张变成了光缆、菊花从一种植物变成了身体部位、NBA的形象大使从姚明科比变成了鸡你太美。
即便青岛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翻了140倍——无论时代怎么变迁,6块钱一碗的路边野馄饨从未掉出过青岛小吃代表的公开评选前三甲。
七年前,我第一次去青岛,从11点排队到11点半,才成功坐上老谢野馄饨的小马扎。
昏暗的路灯下,不透明的馄饨汤呈现了暧昧的橙黄,套着塑料袋的馄饨汤碗给人一种里面全部飘着打湿卫生纸的错觉。
作为一个从小以为馄饨是本地特产的南京人,我曾高度怀疑过这有什么牛逼的。
深夜出门怎么可能只吃馄饨,青岛人通常还要再配一把烤串。
“来都来了。”
在青岛姑娘的强烈安利下我皱着眉头吃完馄饨。果然,从飘着紫菜皮的汤头到散落着碎馄饨皮的汤底,没有任何一点超出了我的预期。
种种表象暗示,野馄饨在我这儿似乎有着配不上盛名的不起眼。
青岛人吃馄饨的习惯是把汤头洒满胡椒粉,在外地人看来有些难以接受。/图片来源:《人生一串2》
这种不起眼的程度到了——如果没有当地人引路你可能连馄饨摊也找不到的情况。
数不清的野馄饨摊,大多无名无姓,他们的牌匾仅仅寄居在一些当地icon型地标的名下。比如海尔路南头、宁夏路小学旁边、海博家具城附近、南京路KFC门口、以及颐中皇冠假日酒店对面。
听着外地游客对这些店名一筹莫展,你或许会更加接近一些“野”字之于与青岛馄饨的要义。
如果仅仅以野摊儿来定义青岛馄饨之“野”,还不能触及它的内核。
谁会在深更半夜特地坐到路边喝一碗平平无奇的馄饨?是出门觅食的馋猫、加班多时的社畜,是酒局脱身的醉鬼、派对散场的女郎——他们都是被野馄饨无私接纳的孤魂野鬼。
无论是6块钱一碗的荠菜馄饨还是8块钱一碗的虾仁馄饨,过量的胡椒面和浓郁的谷氨酸热汤下肚,城市的钢筋水泥开始融化,你的感官步伐开始放慢,刺眼的路灯都会变得柔和。
夜晚的青岛人褪去了白日赋予的社会标签,拎书包的和背LV的拼上了桌、盘卡西欧的和戴百达翡丽的划起了拳。
无论你是腰缠万贯还是家徒四壁,坐上了路边的小马扎,你的身份就只有了食客。
野馄饨是公平的,青岛人在路边欢聚一堂,在路边扬起的尘土与尾气中纵情吞咽的时候,它似乎穿透了身份铸就的壁垒。
野馄饨曾是城市夜晚的终点站,但如今,有人正在把对孤魂野鬼们的馈赠一一收回。
出于行政、卫生等原因,大量的野馄饨摊正在消失,其中不乏一些经营良好的摊位开始退路入室,把野馄饨三个字写上招牌,从一个灰头土脸的摊位变成了有头有脸的餐厅。
他们像被招安的梁山好汉,属于户外的张力被收敛起来,一切服从经营发展的需要。
最著名的老谢野馄饨,摆摊时期名字叫做老谢烧烤。
这似乎是一件好事:流动摊位变成门面,既方便管理、保障卫生,还避免了食客经受风吹日晒,就着汽车尾气喝馄饨。
但对青岛人来说,即使摊主和口味丝毫未动,仅仅是转变了经营场,也有超过五成的青岛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对,直言店面让野馄饨变得不再正宗,把最核心的“野”字抹杀了。
八九十年代的青岛刚刚搭上发展快车,日本海和太平洋的热流涌入这座港口城市的时候,穿着不合身西装的生意人开始用大哥大拨通跨洋电话。
当闹市的霓虹灯第一次亮了通宵,野馄饨应运而生,让每一个在深夜出没的青岛人卸下自己的疲惫。
最早的的野馄饨叫做夜馄饨,连摊位也没有,它们属于走街串巷的挑子和吆喝,慢火熬煮骨汤的香气和灯红酒绿弥漫在一起。
无论酒后还是加班,一碗掺着过量辣椒面的馄饨下肚,热汗由内而发,叫人愉快。深夜果腹的街头野生小吃就这样介入了时代的洪流,青岛夜生活的原始记忆就这么沉淀到了馄饨汤底。
再后来,馄饨挑子变成了路边餐车,馄饨也给利润更高的烧烤啤酒让路,躲在了菜单末尾的主食一栏里。
没变的,只有它们的“野”。
青岛人根据记忆,执拗地把野馄饨的名称移植给了这些在深夜售卖馄饨的餐车摊子。
一个“野”字包裹了没有被时代荡涤的生活方式。
这里有着不同于格子间里的随意。围着摊位的男男女女套路娴熟,先喊老板下一碗馄饨,然后抄起铁盘挑串儿。这样的场景在青岛的每个路口和桥洞重复上演,每个人都能在馄饨摊上获得自由。
几口啤酒下肚,青岛的男人们便会开始在野馄饨摊位上提高音量,开始他们的演讲,他们无所畏惧,因为在野馄饨摊上,没人在乎你会吹出什么。
啤酒输液这种野玩意也只能在青岛的路边摊看到。
作为是一个饱受地图炮的省份,山东的乡土气息和繁文缛节被人反复取笑,仿佛这个地域所有热情和豪爽都是被吹胀的。
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教会了人们克制,而青岛的道教发源让这里变成了例外。
这座城市像一只穿云箭一样,刺穿了齐鲁大地庄严的豁口,它是衬衫革履的程序员队伍里混进的嘻哈男孩,用oversize蔑视了所有伪装出来的拘束与得体。
在青岛夜晚的路边摊上蹲下来,卸掉所有的沉重和社会身份,你就算是真正介入了这个城市的自由灵魂。